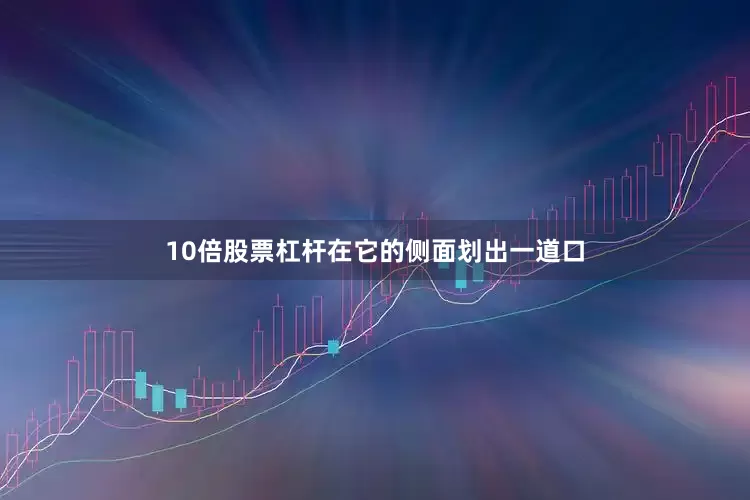在今天看,谁能参与政治,大概是制度和规则说了算。但在两千年前的汉代,政治这回事,还真不是只属于那些坐在朝堂上的士大夫。很多时候,朝廷之外、山林之中,那些不入仕、不挂职、不做官的读书人——也就是“处士”——也能对国家政局产生不小的影响,甚至走上改变政治格局的前台。而要理解这种现象得从一个关键背景说起:儒家如何一步步成为汉代的“正统”思想。
这个过程不像课本上那样简简单单一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能说清楚的。汉初其实并不特别推崇儒家。刘邦本人粗略豪放,他曾当众嘲笑儒生走路慢,说话一板一眼,甚至骂他们“腐儒”。而西汉初年主流的政治思潮,其实更靠近“黄老之术”——讲究无为而治,重视节俭、顺其自然。这一点从文景时期的政策走向就能看出,整个国家在轻徭薄赋、养民休息上做得很彻底。
但问题也就出在这儿。等国家基本稳定、经济积累起来后,汉武帝上台,他的野心显然不是只当个守成之君。要扩张,要统一,要强军强政,黄老那一套显然不够用了。于是,这时的董仲舒站了出来,提出了那套“天人感应”“大一统”“君为天子,臣为人臣”的儒家政治哲学。这个时候,儒家思想不只是道德教化的工具,更是一种国家治理的“理论武器”。汉武帝听了觉得靠谱,于是一锤定音,正式把儒学捧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
从那之后,局面变了。
不仅是朝廷里的官员开始“讲儒”,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也逐渐朝着“唯儒为上”倾斜。尤其是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以后,国学教育正式制度化。你想当官?先读《诗》《书》《礼》《易》《春秋》。你想被地方举荐?必须在儒家价值上表现出“孝”、“廉”、“忠”、“直”。这时候,原本在民间的读书人们,如果通儒术、讲义理,哪怕没有背景、没有门第,也有可能通过察举制度进入官场。
而那些暂时没被选上、或压根没想走仕途的处士,也不是就闲着不管事。他们在地方上讲学、授徒、著书,甚至通过书信、门生、舆论等方式,参与到政治讨论中。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为“横议之士”——不在朝中,却对朝政评头论足,有时还能左右舆情,影响决策。这种“在野议政”的传统,其实从战国末就有苗头,到汉代被儒家价值进一步放大。

可以说,正因为儒学成为了国家的统治思想,才让这些以儒家为思想根基的处士群体拥有了“发言权”。他们说的话、写的文、讲的义理,在社会上有影响,在皇帝和大臣的眼里也不再是“闲话”。有些人甚至因为声望太高,被朝廷下令征召,像汉文帝时期的贾谊、东汉的李膺,原本都不是体制中人,却因为“言有可采”被破格录用。史书中记载,汉文帝曾因一位处士“贤良方正”而特地召见,足见这类人群在当时确实有“被看见”的机会。
不过,别以为这种政治参与都很顺利。随着东汉后期政治腐败加剧,宦官专权、皇帝昏庸,处士与体制的关系也开始分裂。一方面,他们继续在民间讲学清议,甚至形成了“清流”派;另一方面,他们的言论也逐渐触怒了权贵,党锢之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简单来说,就是一部分清流处士因为不断抨击朝廷黑暗,被当权者视为“党人”遭到打压。
但即便如此,处士的影响力还是没减少。相反,因为他们被打压、被封杀,反而更凸显出他们所代表的那套儒家价值观与当时腐朽政治之间的冲突。很多后人看待这段历史时,会觉得处士清议是一种“救亡图存”的尝试,它未必真的能改变政局,但它确实在精神上撑起了士人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
从这个意义上说,处士能参政,并不是因为他们“幸运”地被选中,而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儒家思想成为了一种“权力通行证”。只要你掌握了这一套,你就有可能成为被听见的人。而汉代,恰好是这种机制逐步建立和固化的关键阶段。
对后来两千多年的中国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文化选官制”的雏形。从汉代开始,读儒书、讲儒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变成了士人阶层的必修课。不论是处士、议士,还是正式的官员,他们的出发点和表达方式都越来越趋同。汉代给了处士们舞台,也默默划定了参与的“话语边界”。而这个边界,正是儒家所提供的理论框架。

汉代的政治舞台,本该是士大夫的专场。但偏偏在那个时代,一批既没有官职、也不属于既定体制的“处士”,却频频出现在政局的风口浪尖上。这不是偶然,更不是“破格录用”那么简单,其中的过程,说白了,是一场长期存在的“体制缝隙”被主动撬开的结果。
说回到现实。处士这个群体,从来就不是一块整齐划一的牌子。他们有的身处山林、讲学著书,有的活跃于地方、声望极高,还有一部分人,其实原本就是被排除在仕途之外的“边缘知识分子”。他们不入仕,并不代表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相反,越是不能进场,他们对局势的评论越犀利,影响也越具穿透力。
而这种影响,是有迹可循的。
西汉初期,虽然朝廷还没来得及给“处士”正名,但一些地方诸侯、郡守其实早就开始通过私人交往的方式吸纳他们的意见。地方缺人才,处士成了最方便的“智囊库”。《史记循吏列传》里记载,很多太守在上任之后,第一件事不是整顿军政,而是去拜访本地知名的隐士、儒生。汉景帝时期有个叫龚遂的人,被称为“民间智者”。他就是典型的处士,没在朝廷任职,却能因“能言治道”被推举入朝,从地方直接走进了中央。
到了汉武帝那一代,整个风向变了。因为儒学被正式推上国家意识形态的高位,读儒书的人就有了“被需要”的资格。察举制度开始以“贤良方正”“孝廉有德”为主要标准,而这两项最常被地方官和百姓推荐的人选,恰恰就是那些在地方有口皆碑的处士。民间声望反过来成了一种政治资本。
但这套制度并不完美。朝廷能给出的官位是有限的,处士的数量却在快速膨胀。东汉时期,《后汉书》用一句话形容这种局面:“处士山积,学者川流。”换句话说,有资格但没位置的人越来越多。这时候,处士开始走出一条“制度之外”的参政路径——清议。
“清议”这个词,听上去像是文艺圈的风评,实际上在东汉是一种半公开的政治表达形式。它既不是官方奏章,也不是民间请愿,而是一种围绕时政人物、政策、风气进行的公共讨论。说白了,就是一群读书人凑在一起,对谁该当官、谁该下台、哪个政策不合理,发表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竟然能传到朝廷耳朵里,甚至影响到皇帝的决策。
比如李膺这个人,就是靠清议站上了历史舞台。他原本只是太学中的一个“清流头目”,没有正式的高官身份,但因为敢说、敢评,被视为“士林共主”。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有一段话说,“天下之士,皆以李为宗”。这不是文学夸张,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风向。只要李膺认为某人不可任用,那人即使被朝廷提名,也可能因为清议压力被搁置。

当然,清议不是没有代价的。东汉后期,宦官集团在朝中横行霸道,清议这套“舆论监督”机制,直接戳到了他们的痛点。于是,166年和169年,连续发生两次“党锢之祸”——很多处士、清议领袖被列为“党人”,被捕、流放甚至致死。李膺本人也是在第二次党祸中被捕、死于狱中。但即便如此,清议之风并未熄灭。反而因为打压,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士人共鸣。
关键在于,这一切并不是靠制度推进的,而是靠文化共识维系的。儒家讲仁义、讲道统、讲士人对天下的责任,而处士正是这一价值体系的坚定实践者。他们不靠官职说话,而是靠“道义”的分量。正如《后汉书》中另一处记载:“士有清行者,虽未仕进,众皆推而重之。”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哪怕没有官方任命,处士的声音也能成为政治判断的参照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处士的参政方式,不是靠走“正门”,而是靠在“侧门”发力。他们通过清议、声望、弟子网络、著述传播,构建出一套属于自己的影响力场域。这种方式不依赖官阶、不倚靠门第,而是依托于儒学框架下的“道德信誉”。
而儒家思想之所以有这种魔力,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以衡量权力正当性、官员清廉与否的公共标准。只要你讲得通《论语》,行得正“礼义”,哪怕不是官员,也能获得认可。这就让处士在某些特定时刻,成了比官员更“有分量”的公众角色。
这种现象在东汉末年尤为突出。天下大乱,朝廷腐败,传统士大夫群体一部分被收买,一部分被边缘。而处士群体反而因其“在野”身份,变得更具公信力。很多后来的名将、谋士,其实都出自这些“非官方”的舆论圈。比如荀彧、郭嘉,早年都曾在名士圈子中活动,后来才被曹操、袁绍等招入麾下。
总的来说,汉代处士之所以能参政,不是因为某个政策特别开明,而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已经被儒学深刻塑形。在这个系统中,道义可以凌驾于权力之上,而读书人,一旦掌握了这套“话语密码”,就有资格对政局指手画脚,甚至改变历史进程。

一件事发生得多了,它就不再是偶然。处士在汉代能频繁“插手”政事,不是因为他们谁运气特别好,而是因为当时的那套思想话语,已经不知不觉给他们“开了权限”。
这种权限,不是由皇帝亲口授予,不是诏书上盖了章,而是藏在无数诵读《论语》、《尚书》的私塾课堂里,藏在朝廷对“贤良方正”的偏爱里,甚至藏在百姓对“清流”二字的敬仰里。表面上看是处士参政,实则背后站着的是一整套已经被国家正式认可的儒家价值系统。而当这种系统变成了官方标准,谁掌握得越深,谁就越有可能在政治上说得上话。
可这套话语体系并不是一开始就牢不可破的。早期汉朝其实挺“佛系”的。刘邦不爱听文人讲大道理,文帝景帝也更倾向于黄老那一套,讲究无为、休养生息。但到了汉武帝那儿,风向彻底转了。董仲舒那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儒学理论,给了皇权一个“神圣合法化”的外壳。儒家不再只是讲修身齐家的道德课,而成了国家治理的意识形态。
这时候,处士群体的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
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汉武帝开始,朝廷在选人用人上更看重“学术背景”——尤其是儒学出身。察举制度要求地方推荐“孝廉”“贤良方正”,这些标准说穿了就是在考查一个人是否通经、是否懂礼、是否能把儒家那套道德逻辑实践到生活和为政上。于是,哪怕一个读书人没有官职,只要他在地方上讲学、授徒、行得正、坐得端,他就有可能被“举荐”。他不需要进士出身,也不需要门第背景。他只要会讲“仁义礼智信”,就具备了被朝廷认可的可能。
这种“文化选拔”机制,其实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体系。它把民间读书人纳入了政治潜力库,而他们能被纳入,是因为他们说的是“标准答案”——那就是儒家话语。
所以很多处士没当官,但他们讲的话、写的书、发表的看法,却能在社会上掀起不小的浪花。有时候他们一篇评论就能让一个官员仕途受阻,一封上书甚至能影响政策走向。而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不是靠人脉,也不是靠权势,而是靠“道统”正、义理清。
这时候,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工具,它已经变成了衡量“谁有资格参与国家事务”的价值标尺。谁掌握得深,谁就站得稳。谁说得动人,谁就“有德者居之”。而处士恰恰是这场文化权力博弈中的天然受益者。

进入东汉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尤其在宦官势力膨胀、朝政腐败的时候,很多体制内的士人被迫沉默,反倒是处士——这些不在体制内、但仍有道义声望的人开始发声。他们没有职位,但他们有“清议”的平台,有门生故旧的支持,有道义的背书。他们在地方讲学、在门下聚徒,甚至在士人圈层中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场。
李膺、陈蕃这些人,就是在这种舆论场中脱颖而出的。他们原本只是“在野名士”,但因为敢言、能言、讲的又是“正统儒理”,很快就成为朝廷不得不重视的声音。他们不靠官职说话,而是靠“道义地位”发声。而这种地位,在那个时代,是比职位更有威慑力的。
但话说回来,这种文化权力也不是没有边界的。清议太盛,势必触怒既得利益者。东汉末年接连爆发的党锢之祸,就是这种舆论与权力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处士、清议领袖因为挑战宦官集团,被打成“党人”,甚至死于狱中。表面上看是失败了,但实质上,他们的死反而加固了“清流”的道义形象,让他们在士人群体中声望更高。
从这个角度看,汉代的处士参政其实是一种“文化资本变现”的过程。他们用的是话语影响力,不是实际权力;他们靠的是社会认同,而不是制度授权。可偏偏就是这套看起来“虚”的东西,能在某些关键节点上,撬动政治格局。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文化权力的延续并没有随着东汉的终结而消失。魏晋的“玄学清谈”、唐宋的“士人风骨”,其实都能在东汉这套“儒家话语 + 处士影响力”的模型中找到源头。可以说,汉代的这场文化政治实验,不仅为“处士参政”提供了现实路径,也为后世中国建立一种“以文化制衡权力”的传统埋下了伏笔。
所以,从汉代开始,谁能说得动人、谁能讲得通义理,谁就有可能左右政治。不管你是不是士大夫,不管你有没有官职。只要你占据了“道统”的制高点,就能成为那个时代的“意见领袖”。
而在那个讲究“礼治”的时代,道统就是权力的另一种形态。处士掌握了它,也就掌握了一种“在野权力”。
大牛时代配资-炒股的杠杆平台-正规实盘股票配资-在线股票配资查询门户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